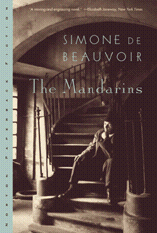|
|
|
| 找題材與 |
|
一個作者要尋找題材,身邊的人、事、物,自然會成為第一手資料,可是,把一些故事,特別是兒女私情,不經修飾剪裁而發表,有時會產生很大問題。
法國著名哲學家兼文學家西蒙波芙娃(Simone
de Beauvoir)的小說【The Mandarins】,是一個很好的例子。西蒙波芙娃與美國作家納爾遜柯甸(Nelson
Algren)曾經是情侶,但西蒙波芙娃的愛情觀十分奇特,她的「第一號情人」是存在主義哲學家沙特(Jean
Sartre),二人終生也沒有結婚,只是保持親蜜關係,但他們卻不反對另一方與第三者來往,當波芙娃與沙特仍然是愛侶時,波芙娃還跟柯甸一起旅行。後來波芙娃把自己的情史改編成上述那本小說,並且憑此奪得一個文學獎。這小說最先以法文出版,不知情的柯甸還向波芙娃道賀。在小說被翻譯為英文後,柯甸極為憤怒,並且寫了〈西蒙波芙娃之問題〉一文抗議。
在中國也有類似的例子,郁達夫把自己的情慾掙扎寫成【沉淪】等小說,他筆下主角的心理,多表現出過敏和妄想的單戀,甚至有性變態的心理。後來他與王映霞發生了一段曲折的感情,二人經常離離合合,可是郁達夫卻將這段情史公開在書報上,導致了王映霞的反感和兩人的決裂。
也許,以上的問題不是情史應否成為寫作題材,而是由什麼人去寫和怎樣去寫。西蒙波芙娃與郁達夫均非保守人士,他們都有十分獨特、甚至是自我的愛情觀。我想,即使他們不以真實人物入文,而只是虛構一些故事,看不過眼者仍會大有人在。
除了情史以外,還有其它具爭議性的題材。臺灣作家歐陽子曾經因寫了一個真實故事而受父親責備,歐陽子的父親是臺灣大學法學教授,有一次一位成績不大好的學生瀕臨被開除之邊緣,那學生的媽媽到老教授的家求情,後來歐陽子將這件事寫成文章發表,她的父親十分不悅,說那位媽媽和那學生讀後會感到難堪。其實,歐陽子並沒有對當事人下價值判斷,如果那老太太不認為自己做法不對,那又怎會難堪?若歐陽子真的在文章中隱含了價值判斷,中國人這種「走後門」的習慣,不是應該值得反映與反省嗎?
也許比較好的寫法,是綜合一個群體現象去寫,而不是針對某一個人,不過,這也不能避免一些人會反應過敏。臺灣文人陳若曦曾經因為政治理想而回歸中國大陸,然而她經歷過文化大革命後便離開中國,她寫了不少反映中國問題的書,其中一部名為【城裡城外】,在小說中她描述中國人都是一窩蜂地要離開。小說出版後,不少朋友問陳若曦為何把他們的故事搬出來。其實,當時那麼多人向外跑,自然每一個人都以為是影射自己。
作家不能只是將現實搬上紙張,反之,他們需要改造現實,這裡所牽涉的問題,有美學的層面,也有倫理的層面,後者是關於保障別人的隱私權。一方面,我不贊成拿人家作為自己獨特愛情觀的註腳,但另一方面,我也不認為為了人家好過一點,而對於一些文化、社會問題隱藏起來,作家,不是社會的良心嗎?
2000.1.5
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