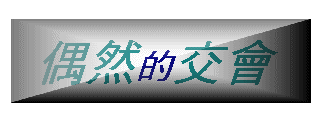|
|
我十分喜愛徐志摩的一首詩:「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,你有你的,我有我的,方向。你記得也好,最好你忘掉,這交會時互放的光亮。」那種瀟灑飄逸,一洗很多中國詩詞對悲歡離合的無奈與傷感,例如「人有悲歡離合,月有陰晴圓缺,此事古難全」,「天之涯,地之角,知交半零落」,「悲歡離合總無情,一任階前,點滴到天明」,「樽前一唱陽關曲,別箇人人第五程。
尋好夢,
夢難成,有誰知我此時情。枕前淚共階前雨,隔了窗兒滴到明」。 人生中很多聚散都不能自主,但與其浸溺於離愁別緒的苦海中、或是懸浮在無盡追憶的真空裡,何不去捕捉那由因緣而生、只是交會一刻時互放的光亮? 因緣,有外面的因素和裡面的緣份,即是客觀條件和主觀選擇,世間的人事物走在一起,可以看成是偶然,這偶然的機遇可能就此擦身而過,但在她擦過我身的那一刻,我把她緊緊抱住的話,這「偶然」便變成「安排」。 因緣又豈是無情?千百年來,她像一位望子成龍的慈母,又如一位孜孜不倦的嚴師,不斷為人間送出「偶然」,期望這些「偶然」終歸變成「安排」,儘管無數「偶然」真的只落得「偶然」。 為了以下一個故事,我常常讚嘆那神祕的因緣:在一八九九年,一位名叫哈辛(Childe
Hassam)的年輕美國畫家,去了法國巴黎習畫,他搬進了一間從前也是一位畫家居住的畫室,人們告訴他以前的畫家是一個瘋子。上一位畫家留下了一些作品,哈辛仔細地觀察那些作品,發現那位「瘋狂的畫家」要去描繪自己的感受,而不只是光光記錄影像,哈辛認為那位畫家正表達了自己一直嘗試去表達的東西,於是哈辛沿著這路徑發展自己的藝術風格,後來成為一代大師。那位所謂「瘋狂的畫家」,就是印象派大師因羅(P.
A. Renoir)。兩人從未謀面,因羅卻不自知地成了哈辛的啟蒙老師,哈辛住進因羅的畫室只是偶然,哈辛可以把因羅遺留的「垃圾」扔掉,但他把握了這一刻無心的交會,從而在畫壇上大放異彩。相反,一些人縱使有機會進入名牌大學,受名師指導,卻依然不能成材,套用兩句廣東俗語,那是「捉鹿不識脫角」、「在城隍廟附近不求簽」,「偶然」終歸就只是「偶然」。 為自己生命中無數的「偶然」,我再次歌頌那有情的因緣。十多年前,偶然地澳門的鄭小姐幫助我謄正文稿和將它投給報社,開始了我十幾年的筆耕,現在即使沒有良田千頃,也是靈糧豐足;十年前,偶然地在西南浸信會大學的黃小姐賣了一套藝康鏡頭給我,憑著它,我在這十年中捕捉了很多稍縱即逝的美好形象;八年前,偶然地在大學電腦中心跟顧問幾分鐘的閒聊,讓我的眼光由侷促的一隅,通過電腦網路,延伸到海闊天空;幾年前,偶然地跟約翰貝倫斯(J.
Behrens)教授談起自己的理想,結果他帶我來到一級研究所,攀登山連山的知識險峰…… 現在,雖然知交半零落,但我仍然感激那交會時互放的光亮。 一九九八年三月
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