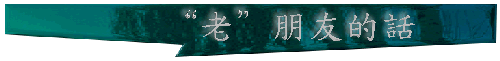
許多年青人都逃避那些「白頭宮女話玄宗」、「王謝堂前之燕子」的老人,但我卻愛跟美國的老人家聊天,因為很多美國老人都告訴我一些課本上不可以得到的經驗與歷史。
占士冬是我最近結識的「老朋友」,他是大學中電腦部門的主管,我任職研究助理,需要很多電腦應用的東西,所以找上了他。
他不像一般人那樣,公事談完後就「拜拜」,他對我說了很多故事。占士冬原本在一間科研發展機構任職,但不幸被辭退,他說自己對那機構和整個美國的科研制度,都十分不滿意。占士冬慨嘆現在有更多人從事科研,可是普遍水準卻下降了,他批評許多科學家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,只是但求塞進電腦的資料變出報告來,有論文可交便算。然而現在科學就是權威,有誰能管得?
他又指美國的一些跨國企業,主宰著人類社會的方向,但是那些高層領導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,他們只顧短線利益,忽略了長遠的人類幸福。而且,企業家和科學家一樣,也是不能接受指摘,占士冬說:有誰會願意承認自己走了二三十年的路是錯的?
占士冬的話,令我想起了一位經濟系學生的意見,他說從前的暴政是「橫的暴政」--
掌權者對同時代但不同地方的人施加壓迫,但今天卻出現了「縱的暴政」--
對不同時間的人,亦即是對我們的子孫加以逼害。現代科技不斷污染環境與消耗能源,我們的後代會不會出錢買氧氣,和用馬來拉沒有汽油的汽車?美國企業和政府不斷高築債台,在九十年代美國國債會滾至一兆億美元,美國人的後代怎樣去償還?但有誰敢逆流而上、力挽狂瀾?
占士冬指斥科研及商業權威有不少盲點,這點我可以在課堂中經驗得到。有一次教授用投影機放射講義,但投影機距離螢幕太近,所以字體小得無法閱讀。其實他只要把機器往後拉便可以解決問題。當時班上有很多人都知道,我也知道,但是直至將要下課時,才有一個學生提出這意見。我是教授的助理,所以事後有人批評我為何不表示意見,我說因為那是常識,所以我期望教授會自己把機器拉後,正因為他是我的上司,我才不好意思出聲。那一次我深深體會到權威怎樣造成盲點!幸好那教授從善如流,但占士冬從前在對抗權威後卻失去了飯碗,我不禁敬佩占士冬那「烈士暮年,壯心不已」的態度。
1990
Navigation
Essay Menu
|
Main menu
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