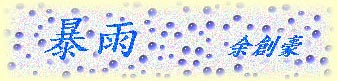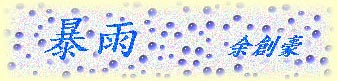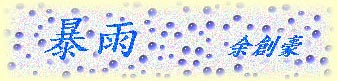
我到加拿大多倫多(Toronto)開會,所以順道前往屋太華(Ottawa)探望
妹妹和妹夫。留了幾天之後,我要從屋太華開車到多倫多,趕搭飛機回美
國。
那天早晨雨勢很大,妹妹替我撐著雨傘,我半邊身子還是濕了。我
的妹妹只是穿著晨樓,我想她也是覺得很冷。
那車子的性能不是很好,開動了引擎後,我要等上幾分鐘,讓引擎
熱起來才敢開車。窗外一片迷濛,在這灰茫茫又冷冰冰的世界,連時間也
好像凝固起來。淅瀝的雨聲蓋住了引擎的聲音,但是在這麼嘈吵的環境底
下,我卻感到有一種浮於世外的安靜。
這凝固的時間和出世的安靜,卻很快被打破了,引擎還在熱身,我
轉頭一望,發覺妹妹仍然在門旁站著!那濕澤的車窗,如一幅印象派的油
畫,妹妹的身影十分模糊,但白色的晨樓卻是極為鮮明,在那一剎,我分
不清那是十年前的妹妹,還是現在的她,抑或是將來在天國中的白衣天使。
為什麼眼前的景象是那麼熟悉?但為什麼在熟悉中又好像有一點特
別?我想起了自己由香港過澳門時,在港澳碼頭妹妹對我揮手送別,還有
在香港啟德機場、在加拿大卡忌利(Calgary)機場……為什麼習慣了離別的
我,在此刻好像很不慣?
我想起了臺灣侯孝賢的一齣電影“童年往事”,在影片中由大陸遷
徙到臺灣的人,最初以為只是在臺灣滯留幾年,就可以回到故鄉,誰知一
停就是一生!每一次在碼頭裡、在機場中,我都以為自己只是暫時出外兩、
三年,我猛然想起:現在我能與妹妹談起的,無非也是童年往事。
引擎熱了,我在開車時,不禁頻頻回首,妹妹揮過很多次手,終於
輕輕地、緩緩地關了門。記得我離開奧拉克荷馬州(Oklahoma)去阿里桑拿
州(Arizona)時,連一個送行的人也沒有,更遑論有人倚門凝望了。
開了一小時車後,我到達了飛機上,將會由一個異國,飛向另一個
異國。雨停了,但另一場暴雨,還在灑著。
﹙原載於“澳門日報”1994﹚
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