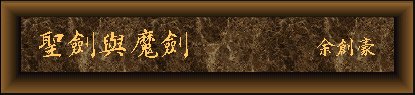
印度聖椎甘地曾說:「生命比所有藝術更偉大,但我更進一步地說,生命接近完美者是最偉大的藝術家,如果沒有一個高貴的生命作為基礎和架構,那麼藝術又算是什麼?」在理論上我十分同意甘地的話,但環顧現實四周,又有幾多個藝術家真的具有高貴的人格、偉大的生命? 在香港我認識一群搞寫作的朋友,有些是自高自大,有些則自憐自艾。在美國讀書時,我的美術系同學只搞怪誕的東西,作品所流露的情緒無非是恐慌、不滿和自我。 人格與風格,人品與作品的關係已是爭論了很久的題目,我沒有什麼高見值得我去插上一言。但甘地所說偉大之藝術基於高貴的生命,也可以倒過來說:藝術塑造生命,生命基於藝術! 法國思想家保羅呂克(Paul Ricoeur)說:當一個人在說自己的故事時,他在不知不覺中塑造著自我形象。英國作家戴安妮修花(Dianne Doubtfire)說:今天你寫什麼,會影響你明天成為怎樣的人。 從前我以為寫東西寫了便是,文章只是我的身外物。但後來我寫多了,便體驗到寫文章是去分析自己的問題、安置自己的感受及前瞻自己的未來,寫文章時我對自己許下了無形的承諾,不知不覺中我會在為人行事上去符合那文章世界中之另一個「我」,那個「我」便成了自己的老師和父親。這過程詭秘得有如武俠小說中劍客煉上一把魔劍,人用劍,而劍亦用人,最後人劍合一。 但願自己所鑄的是一柄「聖劍」,而不是「魔劍」。(原載於澳門日報 一九八九、十二、十七)
| |
Navigation
Essay Menu
|
Main menu
|